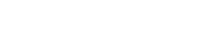刘 波 邹 敏
(1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2四川大学博士生)
摘要:著名藏学家、人类家格勒博士的《康巴史话》,首次以“通史”的编纂体例,流畅的叙述语言,经纬交错的记述方式,全方位叙述了康巴的地域地貌、历史渊源、政治演进、文化发展、民族交融、宗教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康巴历史及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一新著,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康巴藏学研究的空白,又展示和宣传了康巴文化。
关键词:康巴历史;格勒;《康巴史话》
神奇的康巴?伟岸的康巴汉子,动人的《康定情歌》,对普罗大众而言,再熟悉不过,但康巴因何而名?地域如何?历史如何?文化如何?人种如何?康巴汉子特征怎样,《康定情歌》来源是什么?种种问题,除了相关领域的学者外,世人鲜有知晓全貌者,令其如雪域高原一样,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康,来源于藏语Kham,音“喀木”,按照更敦群培《白史》的看法,意为“边地”。所谓的康巴,或者说康区,既是地域名称,也是生活于斯的民众的称谓。就地域而言,康巴是泛指西藏地方丹达山以东的部分地域,在历史上并没有固定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以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国际知名学者,著名藏学家、人类学家格勒博士,出生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的一个村子里,是一位典型的康巴汉子,他学术视野宽阔,学术交流广泛,用文字记述耳濡目染的家乡史,弘扬康巴优秀文化,是他早年的一个梦想。20世纪80年代,格勒博士撰写、出版《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就是这一弘扬乡邦文化梦想的初步实现,他并在中山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如今,格勒博士在此基础上,增益新材料,补充新观点,撰写成内容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康巴史话》,全书洋洋洒洒,凡四十余万言,由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隆重出版。全书装帧设计精美,印刷质量精良,是一本介绍真实的康巴的通识性历史文化读物,涵盖了以上所有的问题。
一
《康巴史话》全书含绪论共二十五章,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经纬交错,叙说了康巴从远古到当代的历史,以政治为主线,涵盖了宗教、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
绪论对康巴之地理环境和区域,康巴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是书的写作目的做了概要性的介绍。第二、三章,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相关资料信息,讲述了远古康区的人类及其生活,南迁康区的羌人,以及见于文献记载的牦牛羌、东女国、美人谷等。第四章讲述吐蕃统一西藏地域后,康巴藏族的形成,区域内各民族的融合,文成公主入藏途径康区的传说。
第五到七章,述及宋元时期中央王朝对吐蕃及康区的治理,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大土司的兴起,尤其详细介绍了德格土司及其名扬天下的德格印经院;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并得到中央王朝认可的茶马互市,及由市而起的茶马古道;藏传佛教各教派在康区的发展与扩张,八思巴在康区的活动及对萨迦派在康区发展的影响,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康区的交融。
第八和九章,讲述明代对康区的治理,固始汗统一康藏地区和“崇教礼僧”政策的推行,中央王朝对高僧大德的封赠,康区寺院的进一步兴起与发展,乳霍尔十三寺的由来及发展脉络,并详细介绍了昌都的四大呼图克图,著名的大金寺和强巴林寺等;明正土司的兴起与发展及鱼通土司的历史概况;康定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纳西族势力在康区的扩张和木天王的由来与历史传说。
第十至十三章主要讲述清朝时期的康区,内容涉及清中央政府对康区的治理政策及变迁,政治上从军事政府到延续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宗教上继续推行“崇教”政策,并述及转生于康区四位达赖喇嘛,格鲁派在康区的发展和木里达喇嘛的形成与发展;汉族、彝族、羌族等民族继续迁入康区和各民族在康区的进一步交融。
第十四、十五章主要讲述康巴人民的斗争精神。长期生活在奴隶制之下的康巴民众,忍受剥削和压迫的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与汉藏民众一样,也一样会展开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斗争,藉此进一步阐释了“康巴汉子”这一名词。
第十六章至二十二章,主要讲述民国时期的康区。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对康区的政治治理、康藏边界纠纷、西藏建省、红军经过康区和博巴政权的建立,格桑泽仁以及格达活佛等民族精英和著名宗教人士对康区治理、康区与中央政权之关系的作为,以及该时期在动乱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系列政治的、军事的和宗教上的事变与事件,揭示了在近代时空环境下,复杂多变之康区社会的众多面相。
第二十三章至二十五章,讲述当代康区。内要内容为康巴进步人士组织之“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及其革命活动,康区迎接解放,民族自治州的建立,以及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所指和康区关于香巴拉的传说,提出“大香格里拉”的地域概念。
二
全书对康区历史上与西藏地方及历代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及其变迁,历代中央政府对康区的治理与管辖做了系统而深入的介绍。
在唐代吐蕃强盛时期,不断向东和向西北攻伐,“康区则成为其军队屯粮和积草的大本营”,吐蕃最强盛时,控制了“青海和西康地区”1。作者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吐蕃对西山诸羌的融合与同化,形成了康巴藏族和嘉绒藏族,因此“康巴藏族张族源并非单一的古代民族,而是包罗了吐蕃和西山诸羌两种不同的底族源文化”2。
统一的吐蕃政权后来崩溃,西藏地方进入诸小国并存的分裂时期,与此同时,唐王朝灭亡,继之而起的宋虽未能将大渡河以西的康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但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仍在不断发展”,茶马互市即于此时因朝廷的认可和提倡而兴起。13世纪,蒙古人的势力迅速崛起,其铁蹄踏入康藏地区,根据《萨斯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作者指出“康区北路一部分地区先归附于蒙古人”。蒙古人通过军事政府将康藏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随后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政策,尊崇喇嘛教,“授予当地上层宗教人士以封号和统治地方的权力”3;同时,诏谕西番诸族酋长内附,对内附者收入世袭官职,成为康区土司制度的开始。此外,忽必烈还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领全藏区的军政事务,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朵甘思宣慰司即设在康藏地区。表明元代确定无疑的对藏康区进行了管理。
明朝对康区为实现“固实封疆,防其侵轶”的统治目标,曾一度采取军事高压手段进行统治,但随之因遭到康区人民的反抗而不得不放弃,延续元代“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和“崇教礼僧”的政策,将“藏区的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各等级”,“并通过他们的影响来安定康区”,从而开始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4。
清朝统治者为了安定西南边疆,数次对康藏地区用兵,并解除了准格尔部对西藏的威胁和侵扰,是为“康区历史的一大转折,从此,包括昌都、感知在内的整个康藏地区纳入了清朝的直接统治”5。土司制度和优崇宗教继续被统治者延续,而作者明确指出清廷颁布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和《钦定西藏章程》以及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强化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及康区的控制,密切了康区与内地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对于边疆安定和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由于清末民初的变局,“康藏地区一时失去控制”,北洋政府曾运作进军康藏,先后成立川边镇抚府,川边镇守使署、西康特别行政区;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并任命刘文辉设立西康特区政府委员会。由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不稳定性,康藏边界纠纷时有发生,康区也因此而游离,其在边疆政治和安全中地位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康区的控制,政治上实现西康建设,并设立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经济上开始康区征税,并设立康藏贸易公司和茶叶贸易公司。正如林孝庭所说,这些计划的实施,使国民政府的商业和经济影响力自1928年首次延生到康区,成为国民政府强化对康区统治的一大成功6。
新中国成立后,康区各地相继解放,依据“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自治,按照民族聚居区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7,“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依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8,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区等规定,康巴地区相继建立甘孜、迪庆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藏族人民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下,真正走进了祖国大家庭。
全书在理清政治关系的脉络的同时,还述及了很多其他内容。如果通过介绍历代统治者对康区的治理,阐述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在康区的兴起和发展情况,以及康区的宗教格局。
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在西藏地区相当兴盛,但随后朗达玛灭佛,藏传佛教遭受打击,藏传佛教随之开始“潜入康区”9。元朝统治者“推崇喇嘛教,促进了康藏地区各地的宗教势力。元代初期,萨迦派(花教)成为藏族地区的统治教派”“萨迦派的势力崛起,并开始伸向康藏地区”“康藏地区最早的喇嘛寺院亦为萨迦教派”;噶举派(白教)的支派噶玛噶举派“在康区自元代开始就颇具影响”10。但整个元代,萨迦派在元代统治者的推崇下,萨迦派在各地佛教中的统治地位是无可厚非的。这一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也形成了藏传佛教与康区原有之苯教共存的局面。
到了明代,由于教派林立,明王朝分封众多的法王,从而打破了“元代萨迦派唯我独尊之格局”,噶玛噶举派继续受到中央王朝的尊崇,在康区拥有众多的信徒;不过此一时期,格鲁派也开始传入康区,并兴建寺庙,对噶玛噶举派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明末清初,“康藏地区土酋四分五裂”,“喇嘛教传进这一地区以后,加剧了诸土酋之间的争夺和竞争。土酋有的支持黄教,有的指出红教,有的指出花教”11,但是随着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以及达赖喇嘛与满清统治者的政治结盟,格鲁派(黄教)很快在整个藏区确立了统治地位,康藏地区兴起了包括著名寺院大金寺、白利寺在内的霍尔十三寺。与此同时,由于清廷对各地宗教首领的册封,康区出现了帕巴拉呼图克图、察雅切仓罗登西绕呼图克图、类乌齐帕曲呼图克图和八宿达刹济咙呼图克图,被称为“康区四大呼图克图”。作者在书中分别介绍了四大呼图克图世系,以及昌都著名的强巴林寺、大金寺、白利寺、寿灵寺和惠远寺等著名的寺院。
此外,本书还包括了很多其他内容,如土司制度及主要大土司在康区的兴起、发展与终结;茶马古道的兴起发展与价值意义;远古人类在康区的发展,西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族源,羌、彝、藏、纳西、普米等众多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在康区的发展和交融;历史上的牦牛羌、嘉绒藏族、木雅娃、夏尔巴人、霍尔巴、东女国、“白狼”部落、附国等,为了解西南地区的民族交融与发展,多样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很多可用信息。
全书在通史之下,还做了很多个案分析和介绍,尤其是在述及“康人治康”时,对格桑泽仁、刘家驹、夏克刀登、邦达多吉以及诺那活佛等人的政治主张和主要活动的介绍,反映了国民政府、刘文辉、西藏地方和康区本土等多种政治势力在康区的较量,透视了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微弱控制力。对格西·阿旺嘉措的介绍,展示了康巴的拳拳内向之心,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敢于与分裂势力作斗争,并坚持自己的主张,力图阻止分裂势力的活动;对格达活佛和平措旺杰的介绍,则反映了康巴人对红军的支持,对革命的推崇与积极参与。
三
在20世纪30 、40年代,随着边疆危机和边疆研究热潮的兴起,曾涌现了一批关于康区的学术著作,如著名学者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12、《西康图经》13,傅嵩炑的《西康建省记》14、陈重为的《西康问题》15、李亦人的《西康综览》16,以及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is Gore)的《川滇之藏边》等17,从不同视角介绍和展示了康区的历史地域、社会变迁和历史沿革。新中国成立后,因边疆研究一度陷于沉寂,康藏研究也无甚进展。80年代以后,随着便将研究的再度兴起,康藏研究又重新获得关注,并日趋活跃。
近年来,随着藏学研究这门“显学”的日益精进,学者对康区的研究也日益跟进,甚至提出“康巴学”的概念,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虽有格勒博士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林俊华的《康巴历史与文化》,谢廷杰、洛桑群觉编著《西藏昌都史地纲要》,以及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等著作相继面世,却没有一部囊括整个康区地域及其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关于康藏史“整体性、系统性和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严重不足”,“是藏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和缺陷”18。《康巴史话》不是纯学术著作,却是一部通俗性的通史著作,也因此而拥有学术著作无法具备的有点——更大范围的读者群,从而能够更好介绍康区,宣传康区,在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康藏史研究缺乏通史性著作的空白。同时,作者的资深藏学背景和对家乡的热爱,丝毫不影响其所述内容的严谨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该书的问世与当今康藏学研究的现状,必然推动一部康区或康藏通史之学术著作的诞生。
就资料使用而言,作者大量使用了有关康藏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公开出版的档案材料,藏汉文史料均有所及,同时还使用了少量的外文资料,这些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与民族等多方面;同时借助国内外已有的学术著作,尽量全面而真实阐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康巴。将史料和已有学术成果转化为通俗而不令人生厌的文本,本书虽不是纯学术著作,但也不是纯通俗性的读物,鉴于二者之间,对一些学术界存在的争议的问题,也略有述及。如关于馆觉护教王究竟属于藏传佛教哪个教派?昌都“护教王”是否从翰些儿吉剌思巴藏卜死后“其爵遂绝”的问题。作者依据汉藏文史料和实地考擦所得,不仅提出了自身研究所得,并开启了相关问题继续研究的空间。对于康区的历史事件,作者进行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如茶马古道的价值意义,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康人治康”思想的实践,康区解放与民族自治州的建立等,真正做到了将真实的康巴展现给读者。
全书的写作体例和谋篇布局也相当合理,叙述内容和线索清晰明了,以政治关系为中心的主线始终贯穿全书,不会给人毫无头绪之感。书末以《格勒博士档案摘录》为附录,方便读者对作者的了解和认识,更便于读者认识、体会和评价全书的内容与价值。
四
是书虽也有其不足之处,如配图尤其是相关历史时期的地图太少,不易引导读者形成直观观感;虽在整体上以时间为基线,却因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时间上的前后跨越,不可避免的出现叙述上的交错重叠;限于体例,对康区宗教的多元性,尤其是苯教与佛教的共存现象,少有涉及等。
总的来说,是书经纬结合,以详实的史料,丰富全面的内容,有详有略,将康巴地区从古至今的多维面相通过文字展示出来,填补了康藏史研究无通史的空白,既具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不愧为是“我国第一部深度挖掘康巴历史文化的典籍”,“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康藏民族演变史、康巴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交融史、民族团结进步史”,一部全面介绍康巴及其历史文化的通俗类历史读物,值得品位和研读。
1.格勒:《康巴史话》,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62-63页。
2.《康巴史话》,第63页。
3.《康巴史话》,第100页。
4.《康巴史话》,第131页。
5.《康巴史话》,第131页。
6.Hsiao-ting_Lin: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6,P129.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7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9.《康巴史话》,第159页。
10.《康巴史话》,第103、106、109页。
11.《康巴史话》,第148页。
12.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藏学研究文集》(中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
13.任乃强:《西康图经》,《任乃强藏学研究文集》(上册)。
14.傅嵩炑:《西康建省记》,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15.傅嵩炑:《西康建省记》,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16.李亦人:《西藏综览》,南京:正中书局,1946年。
17.[法]古纯仁著,李哲生译:《川滇之藏边》,《康藏研究月刊》,1948年,第15期,第5-13页。
18.石硕,邹立波:《康藏史研究综述》,《西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 67-72页。